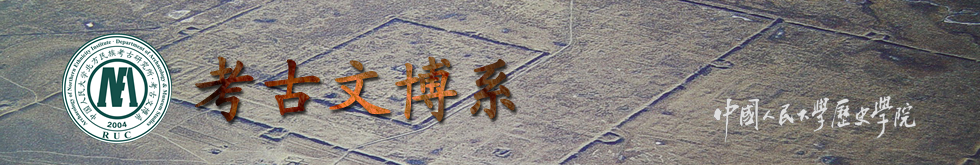
| 热门信息 | |
| 铿锵四人行:“以法律保护文化... | |
| 新疆唐朝墩古城遗址2021年... | |
| 讲座预告 | 《文化遗产保护... | |
| 征稿 |《北方民族考古》(第... | |
| 新书推荐 |《蒙古及周边地区... | |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 | |
| 居延文化研究中心组织专家组考... | |
| 讲座纪要|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 | |
| 最新信息 | |
| 铿锵四人行:“以法律保护文化... | |
| 新疆唐朝墩古城遗址2021年... | |
| 讲座预告 | 《文化遗产保护... | |
| 征稿 |《北方民族考古》(第... | |
| 新书推荐 |《蒙古及周边地区... | |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 | |
| 居延文化研究中心组织专家组考... | |
| 讲座纪要|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 | |
| 考古发掘 | |
| 新疆唐朝墩古城遗址2021年... | |
| 2021年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 | |
| 2020年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 | |
| 2020古北口五里坨段长城遗... | |
| 2020年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 | |
| 顶酷热——慈城考古进行时 | |
| 2020年吉仁台沟口遗址考古... | |
| 2020年宁波慈城东门村遗址... | |
高原文明的历史见证——《蒙古高原考古研究》评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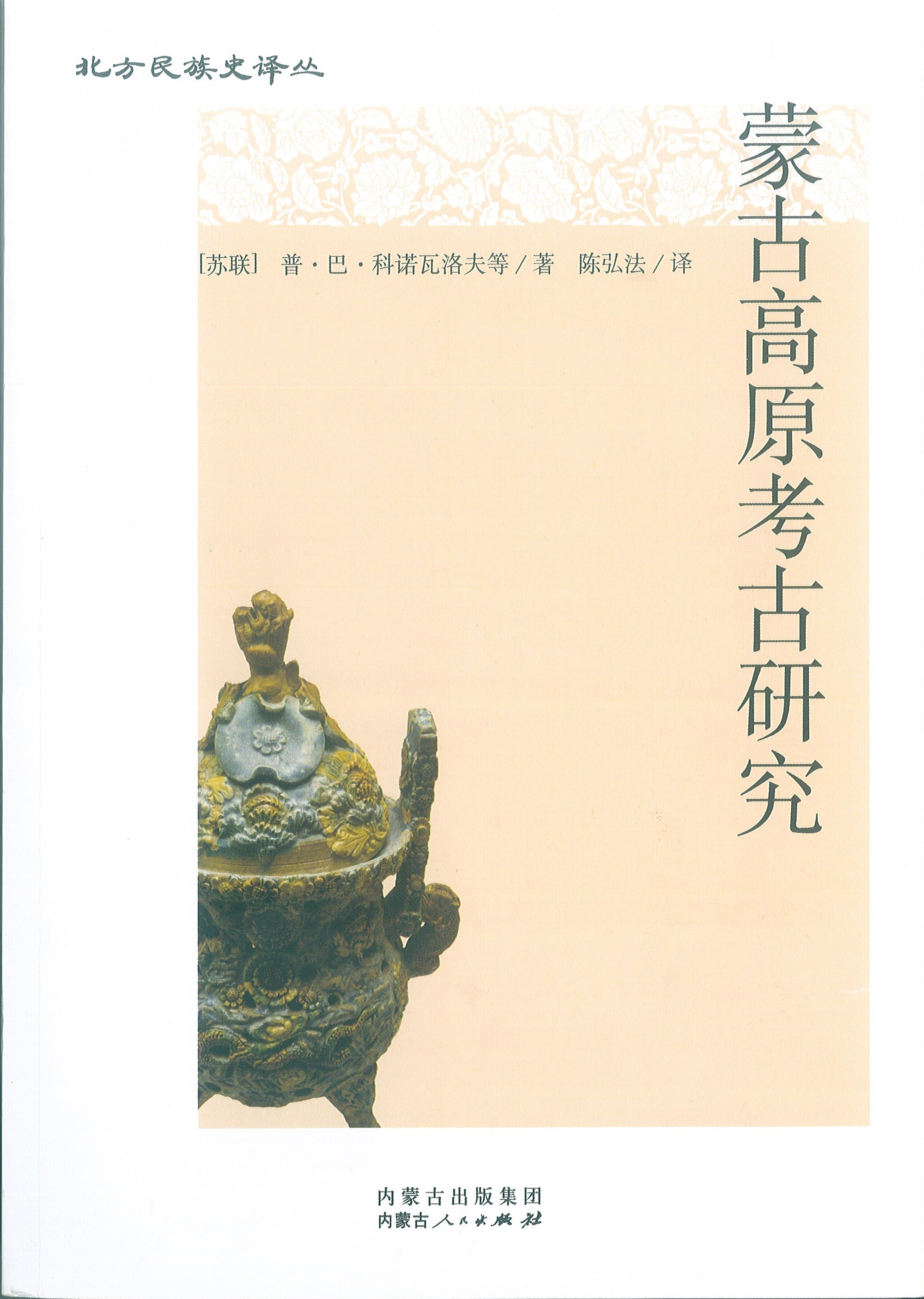
本书约30万字,系陈先生20世纪70至80年代翻译的20余篇俄文考古论文的分类文集,全书共分为六大部分,书的最后还附有陈先生撰写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考古工作的若干情况”的简要介绍。
第一部分为“综述”。这部分译自蒙古国学者达·迈达尔所著的《蒙古历史文化遗存》(1981年,莫斯科)一书。在这部分内容中,系统而概括地介绍了蒙古国境内发现的鹿石、方形墓、匈奴墓、匈奴腰饰牌、突厥墓、突厥“围墙”、突厥石雕像、突厥碑铭和契丹、西夏、蒙古的古代城址等文化遗存的有关情况,可以作为全书的序言。
随后五个部分所介绍的内容既是蒙古高原非常有特色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也是我国北方民族考古工作者长期关注的学术热点问题。
第二部分为“鹿石”。鹿石是一种碑状石刻,是古代的雕塑艺术精品,有刀形鹿石、长方柱形鹿石等。这些精美的鹿石,都经过细致的敲凿雕刻,图案华丽而规范。鹿石是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上的一类重要古代文化遗迹,因碑体上雕刻了夸张的图案化鹿纹样而得名。目前在欧亚草原发现的鹿石有660多通,主要分布在南俄草原、蒙古图瓦、阿尔泰、我国新疆以及中亚地区。鹿石一般或单独向东傲立于赫列克苏尔石堆墓前,或成排列布于石堆或石圈祭坛之内,形成大型祭祀遗址,气势恢宏,体现了草原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同时,有的鹿石上只雕刻了圆环(耳饰)、连点(项链)、腰带,以及刀、剑、弓、弓囊、盾牌等纹样。所以,鹿石一词成为了欧亚草原特定碑状石刻的代名词,并可分出若干类型。
这部分有《关于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鹿石》、《匈蒙考古队关于蒙古鹿石考察工作的若干总结》两篇译文,原文分别面世于1962和1978年,而陈先生早在1979和1984年就将这两篇论文译为中文,只是因刊载这两篇论文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印的《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系内部资料,故而影响不是很大,但这两篇译文无疑开启了我国学界对鹿石这种独具草原文化色彩的遗物的认识和关注。不过目前我国学界对鹿石的专题研究还略显薄弱,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最早公开发表的论文为张志尧的《新疆阿勒泰鹿石之管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4期]。其后较为重要的成果有:乌恩的《论蒙古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潘玲的《论鹿石的相关年代及相关问题》和李刚的《中国北方青铜器与鹿石的若干联系》等。另一方面,国内对鹿石相关论著的翻译也渐次展开。如沃尔科夫所著的《蒙古鹿石》(王博、吴妍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该书对蒙古鹿石的介绍大都是第一手考古学资料,且在沃尔科夫研究鹿石的时代,有不少学者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们探讨了鹿石的分布、分类、年代及意义等问题,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使得鹿石研究更加趋于全面、科学。此外就俄文资料而言,还有《关于鹿石的原型问题研究》《赫列克苏尔与鹿石》《鹿石研究》《鹿石文化起源研究》几篇论文,也是关于鹿石研究的重要成果。
第三部分为“方形墓”。共收录了《蒙古乌兰固木古墓群》和《蒙古昌德曼文化》两篇译文,对1972年在蒙古国西北部乌布苏省乌兰固木市郊昌德曼山发现的两处“方形墓”墓群类型和出土器物进行了描述,并对因后一处墓群而得名的“昌德曼文化”进行了讨论。对于这两处墓地的方形墓,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至少可以细分为圆木木椁石冢墓、圆木木椁土冢墓、石箱墓和石箱石冢墓数个类型。这两篇译文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两点:
其一,为我们认识与乌布苏省毗邻的俄罗斯图瓦地区的乌尤克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1915至1916年,苏联考古学者阿德里阿诺夫在乌鲁格—切姆河谷左岸、毕耶—切姆以及乌尤克河附近发掘了60座墓葬。此后十多年中又发掘了160多座墓葬。1958年,库兹拉索夫将图瓦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命名为乌尤克文化,并将该文化分为两期六个类型,六个类型分别代表斯基泰时期生活在图瓦地区的六个游牧民族。这一观点后来被曼奈奥勒所接受,他在1970年出版的专著《斯基泰时期的图瓦》中,将乌尤克文化分为三期:早期(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中期(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和晚期(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还将墓葬细分为6个类型,8种亚型。乌尤克文化与著名的阿尔赞王陵的1号、2号坟冢也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些考古发现很可能与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具有密切的联系。正如《蒙古昌德曼文化》一文中所言,“蒙古昌德曼文化与图瓦乌尤克文化乃是同一个地域的两种同源考古文化,于公元前7至3世纪存在于中央亚细亚地区的西北部。”如此,我们就将昌德曼文化、乌尤克文化和斯基泰人建立了一种有机的联系,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二,为我们认识蒙古西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乃至蒙古东西两部考古学文化的差异性指出了方向。依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学界已认识到,蒙古国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大致可分为有明显区别的东西两个区域,东部包括肯特山和东蒙草原地区,西部则以蒙古阿尔泰山系及其邻近地区为主。
从这两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来看,石板墓是蒙古东部地区最典型的遗存。其基本特征是以石板为葬具,死者仰身直肢、头向东,随葬品以常见于中国北方的陶鬲和柄部饰动物纹的铜刀为典型。蒙古西部地区则流行冢墓(带有封冢的墓葬),乌兰固木市郊发现的那些方形墓即为代表,墓内出有青铜和铁制的刀、短剑、战锤、骨镞、铜镞和“野兽纹”铜镜、骨饰牌、带扣等。陶器多半是饰有堆塑和彩绘的小口瓶。此外蒙古西部地区还发现了鹿石。就人种而言,石板墓中的人骨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表明公元前1000年,蒙古东部地区居民的人种类型同蒙古现今居民已无区别;而西部地区冢墓中发现的人骨则以欧罗巴人种特征居优势,表明同西方和西北方的古代居民有联系。
第四部分为“匈奴墓和腰饰牌”,有《蒙古呼尼河畔诺音乌拉山匈奴墓发掘记》《蒙古达尔罕山匈奴墓发掘记》《蒙古匈奴墓中发现的彩绘陶器》《苏联南乌拉尔山洞中的匈奴墓葬》《苏联和蒙古的匈奴墓葬结构》《苏联西伯利亚匈奴腰饰牌》《苏联南西伯利亚匈奴青铜器收集品》和《苏联匈奴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共八篇译文,是全书的重点之一。
匈奴考古历来是我国北方民族考古研究的热点,无论是大到对匈奴考古学文化的综合研究,还是小到对具体的匈奴遗迹、马具、饰牌的微观探索,这些译文都是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笔者虽然很难就陈先生的这些译文对我国匈奴考古研究的价值做出全面的评价,但是近年来随着蒙古国高勒毛都等一批匈奴大墓的发掘和相关材料的不断问世,相信对此前翻译成果的借鉴和对比研究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此外,鲁金科所著《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一书已于201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该书的翻译过程中,笔者在内容、手法和技巧上都从陈先生的译作中受益良多。
第五部分为“突厥石雕像、围墙、墓葬和碑铭”,亦是全书的一个重点,共有《苏联额尔齐斯河上游的石雕像》《关于苏联东阿尔泰地区古代突厥人“围墙”的新资料》《苏联中央图瓦的古代突厥武士墓》《中央亚古代突厥文和粟特文碑铭的发现和研究》《蒙古的碑铭学研究》《蒙古却林古代突厥碑铭》和《蒙古阿尔哈纳纳的突厥铭文》七篇译文。
突厥的历史文化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很长时间以来,以历史学研究居多,考古研究相对薄弱。我国目前的相关研究,除了刊布过一些与突厥有关的资料外,涉及突厥考古学研究的论著非常有限,且主要研究对象限于突厥石人、突厥碑铭和突厥金银器这三类遗物。而这部分的译文正好为前两类研究对象增添了鲜活的材料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年来蒙古国最新发掘的几座突厥墓葬的材料公布后,必将对我国的突厥考古研究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六部分为“古城”。收录了《蒙古境内的契丹古城遗址》《苏蒙考察队研究蒙古境内中世纪遗存小分队关于蒙古古城的考古调查》《内蒙古哈拉浩特西夏遗址》和《苏联康堆元代宫殿遗址》四篇译文。
就这部分内容而言,除了笔者在翻译《古代蒙古城市》(商务印书馆,2016年)时,曾参考过陈先生早年刊载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印的《文物考古参考资料》中的《古代蒙古的城市(康堆宫殿)》等译文,并颇受教益外,还有一个游牧和定居的问题不得不提。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游牧民族是否存在着定居和农耕颇有争议。但随着在蒙古高原考古发掘中对游牧民族定居证据的发现日益增多,游牧民族也存在着定居这个观点逐渐得到认同。而城市则与定居具有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定居生活发展的高级形态。由此学界也开始探讨游牧民族经营种植业的证据,以及种植业对游牧民族采用定居生活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应考虑到的是,游牧民族采用定居生活方式乃至修建城郭,或许还与其经营商业具有密切的关系。毋庸讳言,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今后需要继续坚持下去。
记得在谈起《蒙古高原考古研究》这部译文集的书名来历时,陈先生曾语重心长地提到苏联著名蒙古学和考古学家Э.А.诺夫戈罗多娃所著的《古代蒙古》(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献总编辑部,1989年)这部书。该书利用丰富的考古学资料,辅之以古人类学、民族学、碑铭和文字记载材料,对蒙古高原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后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了研究,对蒙古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及其宗教观进行了阐述,并对蒙古境内的古代文化进行了描述。作者引用的俄、蒙、西、中、日等的文献资料共863种,且作者还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对比和分类断代。
陈先生对此书的评价是:《古代蒙古》是一部系统综述蒙古考古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蒙古古代史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重要专著,也许应当说,是唯一的专著。因此,Э.А.诺夫戈罗多娃《古代蒙古》一书对于我国北方地区考古及古代史研究的参考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具有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十分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和延续,与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长期作为农业大国的经济形态关系密切。但中国古代文明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古代文明,一直存在着交流和互动。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时,如果我们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古代文明缺乏深刻的了解,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古代文明。长期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家由于种种原因,都埋头于国内的考古工作,很少有人致力于外国考古研究。因此,中国的考古学家只在中国考古学研究领域有发言权,在中国以外的考古研究领域基本上没有发言权。这种状况,与中国考古学科的地位十分不相称。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首先需要认真了解国外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上世纪末,我国已故的北方民族史专家林干先生就曾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研究有过自己的期望——要收集国内已经发表的并翻译国外的北方民族考古资料加以整理出版。
笔者坚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条道路上,翻译事业定然能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更会对世界文化发展进程产生重大而独特的影响。
滴水穿石,积小溪以成江河。从事考古资料翻译工作达四十载的陈先生,如果能看到此盛况的到来,当是他最大的愿望。让我们像陈先生一样: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让更多学术前沿的译作成为蒙古高原文明的见证!(本文转自“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蒙古高原考古研究》,[苏联]普·巴·科诺瓦洛夫著,陈弘法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定价45元)
随后五个部分所介绍的内容既是蒙古高原非常有特色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也是我国北方民族考古工作者长期关注的学术热点问题。
第二部分为“鹿石”。鹿石是一种碑状石刻,是古代的雕塑艺术精品,有刀形鹿石、长方柱形鹿石等。这些精美的鹿石,都经过细致的敲凿雕刻,图案华丽而规范。鹿石是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上的一类重要古代文化遗迹,因碑体上雕刻了夸张的图案化鹿纹样而得名。目前在欧亚草原发现的鹿石有660多通,主要分布在南俄草原、蒙古图瓦、阿尔泰、我国新疆以及中亚地区。鹿石一般或单独向东傲立于赫列克苏尔石堆墓前,或成排列布于石堆或石圈祭坛之内,形成大型祭祀遗址,气势恢宏,体现了草原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同时,有的鹿石上只雕刻了圆环(耳饰)、连点(项链)、腰带,以及刀、剑、弓、弓囊、盾牌等纹样。所以,鹿石一词成为了欧亚草原特定碑状石刻的代名词,并可分出若干类型。
这部分有《关于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鹿石》、《匈蒙考古队关于蒙古鹿石考察工作的若干总结》两篇译文,原文分别面世于1962和1978年,而陈先生早在1979和1984年就将这两篇论文译为中文,只是因刊载这两篇论文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印的《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系内部资料,故而影响不是很大,但这两篇译文无疑开启了我国学界对鹿石这种独具草原文化色彩的遗物的认识和关注。不过目前我国学界对鹿石的专题研究还略显薄弱,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最早公开发表的论文为张志尧的《新疆阿勒泰鹿石之管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4期]。其后较为重要的成果有:乌恩的《论蒙古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潘玲的《论鹿石的相关年代及相关问题》和李刚的《中国北方青铜器与鹿石的若干联系》等。另一方面,国内对鹿石相关论著的翻译也渐次展开。如沃尔科夫所著的《蒙古鹿石》(王博、吴妍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该书对蒙古鹿石的介绍大都是第一手考古学资料,且在沃尔科夫研究鹿石的时代,有不少学者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们探讨了鹿石的分布、分类、年代及意义等问题,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使得鹿石研究更加趋于全面、科学。此外就俄文资料而言,还有《关于鹿石的原型问题研究》《赫列克苏尔与鹿石》《鹿石研究》《鹿石文化起源研究》几篇论文,也是关于鹿石研究的重要成果。
第三部分为“方形墓”。共收录了《蒙古乌兰固木古墓群》和《蒙古昌德曼文化》两篇译文,对1972年在蒙古国西北部乌布苏省乌兰固木市郊昌德曼山发现的两处“方形墓”墓群类型和出土器物进行了描述,并对因后一处墓群而得名的“昌德曼文化”进行了讨论。对于这两处墓地的方形墓,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至少可以细分为圆木木椁石冢墓、圆木木椁土冢墓、石箱墓和石箱石冢墓数个类型。这两篇译文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两点:
其一,为我们认识与乌布苏省毗邻的俄罗斯图瓦地区的乌尤克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1915至1916年,苏联考古学者阿德里阿诺夫在乌鲁格—切姆河谷左岸、毕耶—切姆以及乌尤克河附近发掘了60座墓葬。此后十多年中又发掘了160多座墓葬。1958年,库兹拉索夫将图瓦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命名为乌尤克文化,并将该文化分为两期六个类型,六个类型分别代表斯基泰时期生活在图瓦地区的六个游牧民族。这一观点后来被曼奈奥勒所接受,他在1970年出版的专著《斯基泰时期的图瓦》中,将乌尤克文化分为三期:早期(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中期(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和晚期(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还将墓葬细分为6个类型,8种亚型。乌尤克文化与著名的阿尔赞王陵的1号、2号坟冢也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些考古发现很可能与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具有密切的联系。正如《蒙古昌德曼文化》一文中所言,“蒙古昌德曼文化与图瓦乌尤克文化乃是同一个地域的两种同源考古文化,于公元前7至3世纪存在于中央亚细亚地区的西北部。”如此,我们就将昌德曼文化、乌尤克文化和斯基泰人建立了一种有机的联系,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二,为我们认识蒙古西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乃至蒙古东西两部考古学文化的差异性指出了方向。依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学界已认识到,蒙古国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大致可分为有明显区别的东西两个区域,东部包括肯特山和东蒙草原地区,西部则以蒙古阿尔泰山系及其邻近地区为主。
从这两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来看,石板墓是蒙古东部地区最典型的遗存。其基本特征是以石板为葬具,死者仰身直肢、头向东,随葬品以常见于中国北方的陶鬲和柄部饰动物纹的铜刀为典型。蒙古西部地区则流行冢墓(带有封冢的墓葬),乌兰固木市郊发现的那些方形墓即为代表,墓内出有青铜和铁制的刀、短剑、战锤、骨镞、铜镞和“野兽纹”铜镜、骨饰牌、带扣等。陶器多半是饰有堆塑和彩绘的小口瓶。此外蒙古西部地区还发现了鹿石。就人种而言,石板墓中的人骨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表明公元前1000年,蒙古东部地区居民的人种类型同蒙古现今居民已无区别;而西部地区冢墓中发现的人骨则以欧罗巴人种特征居优势,表明同西方和西北方的古代居民有联系。
第四部分为“匈奴墓和腰饰牌”,有《蒙古呼尼河畔诺音乌拉山匈奴墓发掘记》《蒙古达尔罕山匈奴墓发掘记》《蒙古匈奴墓中发现的彩绘陶器》《苏联南乌拉尔山洞中的匈奴墓葬》《苏联和蒙古的匈奴墓葬结构》《苏联西伯利亚匈奴腰饰牌》《苏联南西伯利亚匈奴青铜器收集品》和《苏联匈奴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共八篇译文,是全书的重点之一。
匈奴考古历来是我国北方民族考古研究的热点,无论是大到对匈奴考古学文化的综合研究,还是小到对具体的匈奴遗迹、马具、饰牌的微观探索,这些译文都是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笔者虽然很难就陈先生的这些译文对我国匈奴考古研究的价值做出全面的评价,但是近年来随着蒙古国高勒毛都等一批匈奴大墓的发掘和相关材料的不断问世,相信对此前翻译成果的借鉴和对比研究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此外,鲁金科所著《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一书已于201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该书的翻译过程中,笔者在内容、手法和技巧上都从陈先生的译作中受益良多。
第五部分为“突厥石雕像、围墙、墓葬和碑铭”,亦是全书的一个重点,共有《苏联额尔齐斯河上游的石雕像》《关于苏联东阿尔泰地区古代突厥人“围墙”的新资料》《苏联中央图瓦的古代突厥武士墓》《中央亚古代突厥文和粟特文碑铭的发现和研究》《蒙古的碑铭学研究》《蒙古却林古代突厥碑铭》和《蒙古阿尔哈纳纳的突厥铭文》七篇译文。
突厥的历史文化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很长时间以来,以历史学研究居多,考古研究相对薄弱。我国目前的相关研究,除了刊布过一些与突厥有关的资料外,涉及突厥考古学研究的论著非常有限,且主要研究对象限于突厥石人、突厥碑铭和突厥金银器这三类遗物。而这部分的译文正好为前两类研究对象增添了鲜活的材料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年来蒙古国最新发掘的几座突厥墓葬的材料公布后,必将对我国的突厥考古研究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六部分为“古城”。收录了《蒙古境内的契丹古城遗址》《苏蒙考察队研究蒙古境内中世纪遗存小分队关于蒙古古城的考古调查》《内蒙古哈拉浩特西夏遗址》和《苏联康堆元代宫殿遗址》四篇译文。
就这部分内容而言,除了笔者在翻译《古代蒙古城市》(商务印书馆,2016年)时,曾参考过陈先生早年刊载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印的《文物考古参考资料》中的《古代蒙古的城市(康堆宫殿)》等译文,并颇受教益外,还有一个游牧和定居的问题不得不提。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游牧民族是否存在着定居和农耕颇有争议。但随着在蒙古高原考古发掘中对游牧民族定居证据的发现日益增多,游牧民族也存在着定居这个观点逐渐得到认同。而城市则与定居具有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定居生活发展的高级形态。由此学界也开始探讨游牧民族经营种植业的证据,以及种植业对游牧民族采用定居生活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应考虑到的是,游牧民族采用定居生活方式乃至修建城郭,或许还与其经营商业具有密切的关系。毋庸讳言,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今后需要继续坚持下去。
记得在谈起《蒙古高原考古研究》这部译文集的书名来历时,陈先生曾语重心长地提到苏联著名蒙古学和考古学家Э.А.诺夫戈罗多娃所著的《古代蒙古》(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献总编辑部,1989年)这部书。该书利用丰富的考古学资料,辅之以古人类学、民族学、碑铭和文字记载材料,对蒙古高原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后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了研究,对蒙古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及其宗教观进行了阐述,并对蒙古境内的古代文化进行了描述。作者引用的俄、蒙、西、中、日等的文献资料共863种,且作者还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对比和分类断代。
陈先生对此书的评价是:《古代蒙古》是一部系统综述蒙古考古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蒙古古代史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重要专著,也许应当说,是唯一的专著。因此,Э.А.诺夫戈罗多娃《古代蒙古》一书对于我国北方地区考古及古代史研究的参考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具有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十分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和延续,与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长期作为农业大国的经济形态关系密切。但中国古代文明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古代文明,一直存在着交流和互动。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时,如果我们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古代文明缺乏深刻的了解,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古代文明。长期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家由于种种原因,都埋头于国内的考古工作,很少有人致力于外国考古研究。因此,中国的考古学家只在中国考古学研究领域有发言权,在中国以外的考古研究领域基本上没有发言权。这种状况,与中国考古学科的地位十分不相称。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首先需要认真了解国外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上世纪末,我国已故的北方民族史专家林干先生就曾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研究有过自己的期望——要收集国内已经发表的并翻译国外的北方民族考古资料加以整理出版。
笔者坚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条道路上,翻译事业定然能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更会对世界文化发展进程产生重大而独特的影响。
滴水穿石,积小溪以成江河。从事考古资料翻译工作达四十载的陈先生,如果能看到此盛况的到来,当是他最大的愿望。让我们像陈先生一样: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让更多学术前沿的译作成为蒙古高原文明的见证!(本文转自“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蒙古高原考古研究》,[苏联]普·巴·科诺瓦洛夫著,陈弘法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定价45元)
| 友情链接 |
|